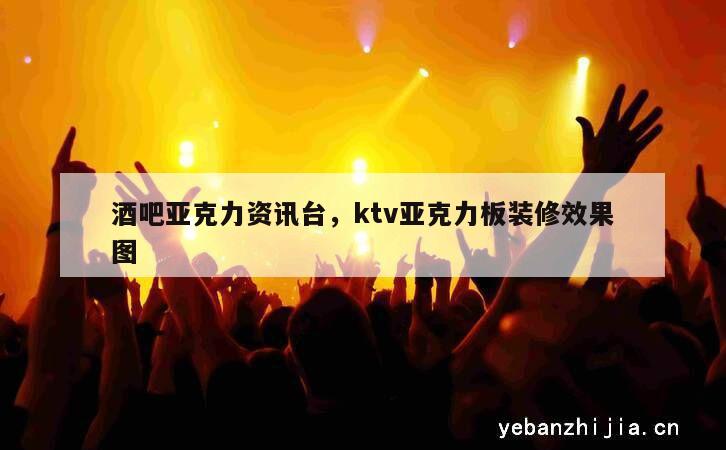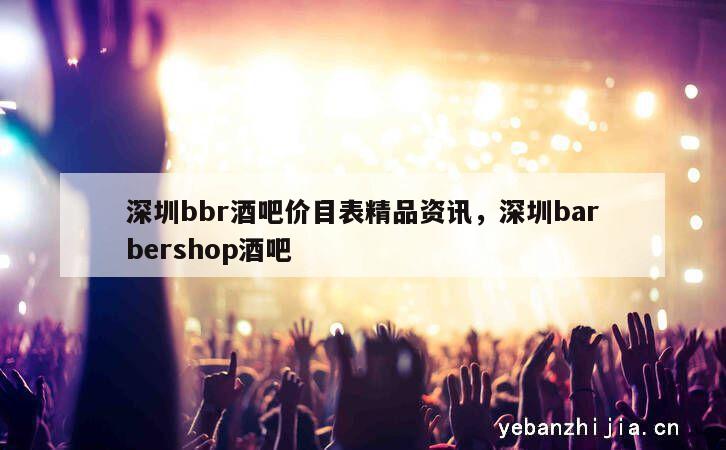昆明半山酒吧都有些什么酒_【昆明1983】张晓刚的左岸宿舍
1983年,张晓刚在昆明市歌舞团工作分得一间宿舍,这狭小而杂乱的房间成了昆明艺术界的“左岸”---------画家、音乐家、演员、舞蹈家……来自天南海北的各路英雄在此高谈阔论把酒言欢,那些充满酒精和激情的日日夜夜和艺术家们的生活状态一起定格下来,永远留在那个时间,那个房间。
毛旭辉《夜晚的护城河》,板上油画,60x42cm,1982
昆明有条塞纳河
一个城市通常都会有一条河流经过,来承载这个城市的思想和文明。昆明艺术家心中的那条河应该会是塞纳河——这条穿过巴黎城市中心的河流,却远隔千山万水地承载着他们对西方文化艺术的一种特殊向往。
1983年的昆明护城河——盘龙江
横贯昆明城市南北的盘龙江,是旧时这个城池的护城河。因为1910年滇越铁路的开通,法国人选择在昆明火车南站附近的盘龙江两岸修筑了宾馆、银行、教堂、邮局、医院等很多具有法式风格的建筑。旁边的街道也一如法国街道一般,栽种着茂密的法国梧桐,而那些有着红瓦黄墙绿色百叶窗的建筑在树荫中若隐若现。隔着几条街就能闻到“南来盛”咖啡馆飘来的混杂着硬壳面包酸气的咖啡香味。这是1990年代之前的昆明一直保留的城市风貌。
在昆明艺术家充满浪漫主义的想象中,盘龙江比任何一条河流都更接近塞纳河的灵魂。他们曾经在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巴黎的空气都充满了艺术。”这让大家充满了向往,巴黎成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艺术家应该去的地方。但这种向往并不具备细节——没有人关心一杯咖啡要多少钱,租一间房子要多少钱,要付多大的代价才能去巴黎,只是一个单纯的梦想,一个精神的故乡。于是他们把流经自己身边的这条曾经的护城河——盘龙江称为“塞纳河”。他们就这样自由自在地任由自己的思想天马行空,在盘龙江边上抬着大碗米线,眼睛看着河岸上的法式建筑,心里已经恍然在巴黎塞纳河边徜徉。
毛旭辉《酒后漫步在护城河岸》,67x62cm,板上油画,1982年
1983年,张晓刚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以后,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一个在昆明市歌舞团做美工的工作,尘埃稍稍落定。到歌舞团报到后,团里分给他一间宿舍。这间宿舍就在盘龙江边,自然就成了“左岸”,也成了昆明当时的一个艺术据点。
左岸的房间
1982年,我平生第一次来到张晓刚的这间宿舍。那是一个有着湛蓝天空和安静暖阳的下午,我和黄洁淳从书林街金鸡塔旁边的一条小巷子来到昆明市歌舞团,周边的小街小巷是昆明最有文艺气质的地方,散落着一栋栋法式风格的小楼,盘龙江近在咫尺。沿着歌舞团宿舍二楼幽暗的走廊走到底,走进了张晓刚的宿舍。掀开门口的帘子,我看到一张长满青春痘的忧郁脸庞,头发很长,穿得邋邋遢遢,记得很清楚的是他居然穿着一条牛仔裤。当时,牛仔裤是一种对传统服饰文化反叛的象征,并不是今天的日常服装。墙上贴着的是他的那一组《阿坝组画》。到今天我还记得第一眼看见这批作品的感觉,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习画画,老实说我其实不是太看得懂,但是觉得和以往看的画太不一样,到今天我还记得有一种强烈的橄榄绿和褐色的调子。那种强烈的感觉似乎可以让你闻到空气里有一种味道。
1983年在昆明,左起:刘智勇,张娅琴,张晓刚,胡晓刚,胡晓钢,孙东风,黄平川,刘湧
这间宿舍除了画以外,好像空间全部被书占据了。在窗子左侧,有一张尺寸不是很大的单人床。记不起那天说过什么,但是这种艺术家的气质和艺术家的生活已经打动了我少年的心。
我读的中学其实和张晓刚的宿舍只隔了一条盘龙江,所以我们有很多生活的场所是共同的。那时,在我们生活的范围内,只有一个新华书店在塘子巷,我经常在逛书店的时候会碰到张晓刚。他对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并没有记忆,所以尽管当时我很敬仰他,可他并没留意到我。每次他在买书的时候,我就会偷偷在旁边看他买的是什么书。我记得我用省下的早点钱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就是看他买了以后才赶紧买下的。他买书的时候很痛快,常常一买就是一书包,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发工资的日子。有时候,我会去附近的滇池电影院看一场晚上10点左右的电影,也常常会看到张晓刚一个人去看电影。有一次我去看通宵场,5部电影联映,竟然发现他也一个人坐在电影院里。那时候觉得他很像从台湾跑回大陆的音乐家侯德健,很有艺术家的气质,我总是暗自在想,如果要能跟他学画画就好了。
我和张晓刚的交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的。由于心生崇拜,我一直渴望跟张晓刚学习画画。我叔叔的一个朋友在昆明市歌舞团搞音响工作,和张晓刚既是同事又是邻居,介绍我去跟张晓刚学习。记得是1983年初秋的一个晚上,我再次走进张晓刚的房间,满满一屋子人,有坐在凳子上的,有坐在床上的,烟雾腾腾。我就这样认真地拜张晓刚为师,学习画画。那天晚上人很多,只记得有一个坐在床上穿着筋筋吊吊的毛衣很瘦的高个子对我说:画画就是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后来知道这个人就是毛旭辉。
1998,张晓刚重返昆明歌舞团的“左岸”房间,在宿舍被拆除之前留下了最后一批照片。
每过一段时间,我就把自己画的习作拿去给张晓刚看,每次看完,他都会言简意赅地指出存在的问题。我至今记得,有一次他从地上捡起一块三合板在上面寥寥画了几笔给我示意素描的黑、白、灰关系。我每次去找他,感觉他都很严肃,像一个生活态度认真的长辈,完全没有后来朋友之间的那种亲切感。后来慢慢知道了当时让我有些心悸的那组《阿坝组画》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名画”。也慢慢知道了这间斗室虽然狭窄,却是昆明艺术青年的“左岸”。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考验,我才被“左岸”的艺术家们接受,他们也成了我亦师亦友的兄长。
在“左岸”的这个房间,无数次看着台子上一组漂亮的静物水果咽口水,却被告知那是张老师画美女模特儿时,才可享用。也无数次在这个房间见证各路英雄高谈阔论、佐酒,继而“高山流水”般地呕吐。也是在这个房间,在帮他收拾房间里的物品运回重庆的时候,他拿起一块落了厚厚一层灰的胶合板吹了吹,是一幅他根据速写绘制的《圭山风景》。也许是上面灰尘太厚,他竟想顺手扔到不要的物品里。我赶紧要求他留下给我。在我21岁的时候,收藏了第一件他的作品,成为张晓刚的终身收藏家,今天这幅《圭山风景》已经被著名的PHAIDON出版公司出版的《ZhangXiaogang》收录,成为了又一个艺术神话。

黑夜中的隐形人
对张晓刚和毛旭辉来说,1983年是个充满了酒精的年份,喝酒几乎是聚会的主要节目。年轻人不仅需要酒解决郁闷,还需要酒带来的兴奋。喝酒带来的激情,仿佛可以超越一切。
1983年,张晓刚描绘自己在昆明歌舞团的斗室里。
单位的正常工作之余,毛旭辉也常常和张晓刚聚在“左岸”的宿舍一起喝酒,大多时候没下酒菜,通常就着一袋胡豆或者花生米,两个人边喝边聊,越聊越兴奋。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他们正喝着,就来了一个朋友,一看他们在喝酒就去买一包花生米和一瓶酒加入,可能喝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朋友,于是又加入进来。人多了,就往地上铺两张报纸,大家围坐在地上,喝着酒,抽着烟。毛旭辉有时会弹着吉他唱些俄罗斯民歌和一些老歌,没有喝醉的人唱着歌用盆接着喝醉了的人“高山流水”的呕吐物,貌似很波希米亚的生活。他们有时也会听一些张晓刚用录音机自己编辑整理的音乐——利用在歌舞团的条件,张晓刚培养了一手编辑音乐的好功夫,直到今天还一直受用。
秋天的一个晚上,毛旭辉去找张晓刚喝酒。喝完一瓶白酒,两人都有点喝高了,决定去“塞纳河”边走一走。两人互相搀扶着歪歪倒倒地一路走着,路上的行人频频回头看着这两个醉汉。他们互相倾述着对现实中的种种不满,一边沿盘龙江的岸边走着。那时,盘龙江的岸边有很多的平房,已经酒醉的毛旭辉和张晓刚以为自己成了隐形人一般,别人看不见他们,而他们却可以像神一样去观察到别人的行为。他们从开着的窗户往里看,看那些房子里的人都在做什么。如果这个房间里的人在读书,那就不打搅他走开了;如果那个人他们看不顺眼,就一脚把门踢开,然后赶快跑,就这样一路捣着乱。那天晚上他们踢了很多家的门,奇怪的是竟没有人来管他们。两个人围着“塞纳河”走了一圈,酒也醒得差不多了,又在江边坐了一会儿,就各自回去了。毛旭辉曾经画过一幅画,是他想象着他和张晓刚在河岸边互相搀扶的背影在黑夜里,在昏昏的月光下。那幅画叫《酒后漫步在护城河岸》,仿佛把那些年的日日夜夜和他们的生活状态定格下来。
1983年,张晓刚于昆明朋友家中
虽然过的是单身汉的自由生活,但这种自由在当时还是非常有局限性的。毛旭辉清楚地记得那时想到爱情、自由都觉得自己有种犯罪的感觉昆明半山酒吧都有些什么酒,时刻感觉到自己有很大的压力。他尽力在写作和阅读当中去找到自由。他写笔记,写到要冲破桎梏,冲破现实,来为自己打气。当一个艺术家希望根据自己的感觉进行创作的时候,如果连自己基本的意识和权利都不能掌控,那是不可能再考虑关于艺术创作的问题的。毛旭辉认为,艺术家不可能过着一般人认为的官方画家的生活,有职业有地位,一边拥有很主流的生活,一边却去从事所谓的现代艺术。那种浓重的悲剧感一直伴随着毛旭辉,他意识到要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就意味着“要去过一种不被人理解昆明半山酒吧都有些什么酒,甚至是叛逆的生活,这是地下的、要遮蔽的、叛逆的、潜伏状态的,必要的时候还要和社会发生冲突”。在那样压抑却又心里异常明白的情况下,大家经常喝醉,用张晓刚的话说,仿佛是泡在酒桶里。大学时的毛旭辉既不喝酒也不抽烟,毕业后,寻找中的怅惘以及无从挣扎的空虚,让他找到了烟酒这种可帮助发泄的工具,而且张晓刚和毛旭辉的烟瘾酒瘾也在互相影响。那几年对毛旭辉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每天都有很激烈的灵魂搏斗,他写了很多愤怒的文章,画了一系列很重要的作品。他总是在喝酒之后骂虚伪的社会,觉得应该像尼采书中写的那样要做一个强大的人,要做怒狮不做羊群,要领着平庸的人找到彼岸。那时候他们看尼采的东西觉得特别过瘾,觉得尼采也像他们一样是一个愤青,书中的每一句话都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自画像Self-portrait》,纸板油画,40x30cm,1983
张晓刚、毛旭辉、潘德海这一群人那时自信甚至有点自负,在昆明看不起什么人。这一年中,他们几个人画了很多画,每次聚在一起喝酒都在讨论艰涩的问题,用愤怒的语言批判社会,批判人们平庸的意识。这个小团体的价值观是看这个人纯不纯粹,“纯粹”是很关键的词。毛旭辉把大家天天挂在嘴上的“苦涩、大气、永恒”这几个词总结为那时艺术人生的标准,达到这个标准的就是哥们儿,是信得过的人。那时候,全国的青年都开始活跃起来,南来北往的人很多,有些人莫名其妙地就来找张晓刚、毛旭辉他们,只要这个人能谈弗洛伊德、谈尼采,谈朦胧诗,那就是朋友,他们就会接待他,带着陌生的朋友到食堂吃饭,晚上再安排睡觉的地方。他们之间不用介绍,来到他们的“窝子”看当代艺术的过客,谈梵·高就是通行证。
1983年留在四川美院教书的叶永青开始带他的第二个班,他一面停留在艺术家的生活中,另一面又要为人师表。他每次离开昆明“左岸”的这群朋友回到四川美院后,越发觉得没有能够交流的朋友,他也开始喝酒。夜幕降临,喝酒的时刻到了,可他发现连一起喝酒的人都没有。四川美院周围有很多防空洞,那是铁路巡道工下班后喝酒的地方,酒是最便宜的老白干,叶永青坐在防空洞酒馆里,身边都是喧哗的工人。叶永青觉得生活真是没有希望,精神也绝望至极,不知道该怎么办,很是苦闷。为打发时间,他开始大量画画,因为受现代艺术流派的影响,画的作品也当然不是学校认可的类型。他最渴望的事情就是回到故乡云南,因为昆明有一帮和他心意相通的朋友,那是个逃避现实的地方,所以他画了很多关于西双版纳、圭山的画表达内心的苦闷和孤独。他想念昆明市中心的那条河—盘龙江,河两岸有他的许多战友,他想念这些在“左岸”的艺术家朋友。
酒精里结束的1983
叶永青和昆明的张晓刚保持着通信。那时候文化界经常有各式各样的文艺青年人来人往,经常有“天才作家”“音乐才女”等奇人从北京或者上海一路发到重庆,叶永青就把他们又到昆明“左岸”,张晓刚又把去了昆明的各种人物再发到西双版纳或者云南别的地方。这些人大多面目不清,来来去去,带来各种文化资讯和各种新锐思想把城市之间地下的前卫文化搞得异常活跃,仿佛要发生些什么大事情。
1984年于昆明歌舞团宿舍内,此时,刚从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出来,正在创作“幽灵系列”。身后的两幅作品是:《初生的幽灵》、《升起的地平线上》
同时,1983年也是张晓刚过得最为疲劳的一年,他的“左岸”宿舍成了昆明的一个艺术据点。渐渐的,毛旭辉、潘德海等昆明艺术家朋友把这个地方当作一个公共的艺术中心,钥匙在门头上,他们都知道,他不在,就自己打开门进去。常见的情况是,张晓刚晚上回到自己的宿舍,已经坐了满满一屋子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了,而且可能有两拨人已经走了,留下了几张借书的借条。他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私生活。经常有很古怪的人半夜来找他,彻夜和他谈人生、谈痛苦、谈哲学;有些朋友失恋以后,半夜也会来敲门,说要住在他那儿,然后彻夜地谈自己失恋的过程。张晓刚原本的生活规律被整个儿打乱了。
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人会来拜访他。有一天晚上,一个朋友带来了1978级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张丰毅。他们坐在张晓刚拥挤的宿舍里,共同用一个搪瓷口缸喝着白酒,展望自己未来的艺术梦想。由于共同的年龄和处境,所以他们针砭时弊,抒发自己的艺术情怀。不久以后,张丰毅就以《骆驼祥子》开始蜚声影坛。那个时候,各地来的艺术家和文化人带来的各种信息和文化在这里交织,他们讨论艺术,畅谈文化理想。很多今天的文化名人都曾经造访过这个小小的据点,杨丽萍、张献、吴文光、肖钢等都是当时的常客。如果当时你偶然闯进张晓刚的宿舍,烟雾腾腾的一堆人当中可能某一位就是今天艺术领域中的重要人物。
1983年,张晓刚(左一)、叶永青(左二)、秦明(前排左一)、杨千(前排右一)于中央美术学院宿舍
这一年,张晓刚画了一批人像,这种肖像创作更多是把他自己的“情感、思想和愿望贯注进去”。这也许就是张晓刚后来创作《大家庭》最早的一个源头。
1983年10月,在心绪最乱的时候,喜欢独行的张晓刚一个人跑到了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待了一个多月,走村串寨与彝族青年一起经历生死洗礼。他喜欢大凉山那种高贵的灰色色调,欣赏那些沉默寡言与大山作伴、与苍白天空对话的彝人。在布拖县,他觉得彝人那种通过酒精独自漫游山巅之外的半神半人的境界竟与自己的生活有几分相像。
从大凉山回来以后,他又回到了酒精生活中。1983年的最后一天,张晓刚喝得酩酊大醉,被从“左岸”宿舍直接送进了医院住院治疗。
[编辑/张墨][文/聂荣庆][部分文字摘于人民美术出版社《护城河的颜色》,聂荣庆著]
更多精彩内容请回顾——
本章链接:https://www.yebanzhijia.cn/news-id-1051.html